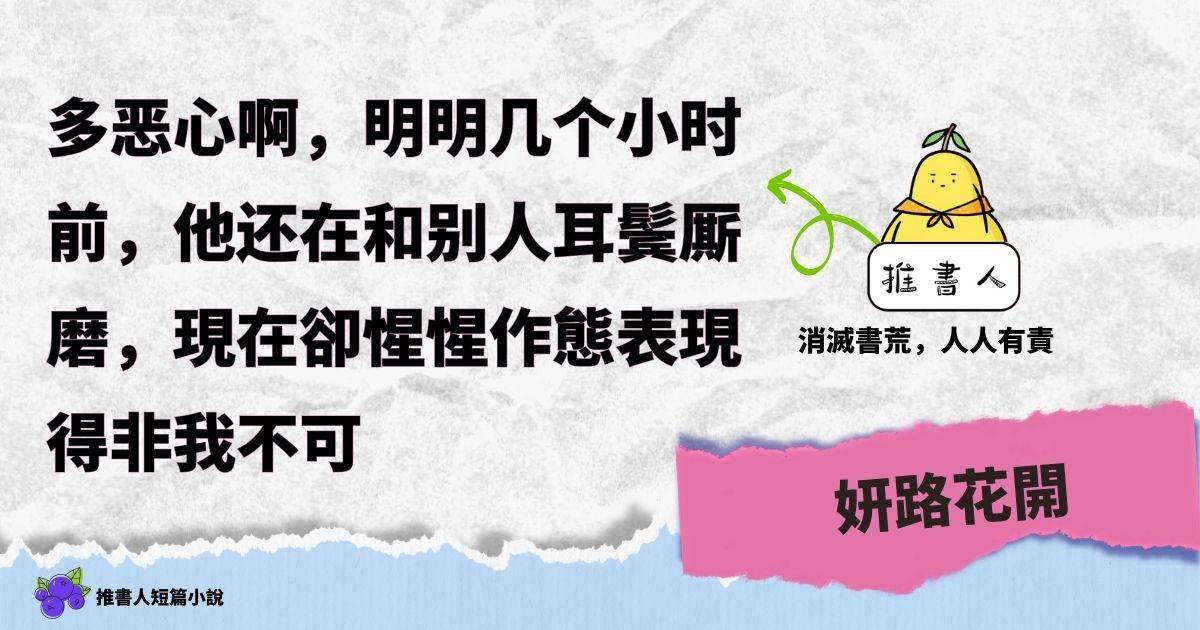《妍路花開》第5章
股權是他在公司的命脈,此刻卻愿意無償轉讓給我。
他仰望著我,姿態再次低到了塵埃里。
我卻突然產生了一種報復的念頭:「太晚了。」
他開口想說「不會」,卻被我從包里拿出的孕檢單生生噎在喉嚨里。
「發現你和肖雪在一起那天,我打掉了我們的寶寶。」
他盯了我許久,好半天才不可置信地拿起那張薄薄的紙頁。
我知道宋延知多想要一個孩子。
一年前他親手做的小木馬,還好好存在準備好的兒童房里。
「陳妍!你的心為什麼這麼狠?」
他退后兩步,目眥欲裂地看著我。
我也望著他,平淡的語氣里夾雜著刺骨的寒意:「你第一天知道嗎?」
很久以前,我們吵得最兇的時候,三個多月沒聯系。
后來,他在去西藏的火車上找到了我,見到我說的第一句話就是:「陳妍,你的心真狠,是不是我不找你,你就不會來找我?」
當時,我的眼淚已經在眼眶里打轉了,愣是一聲不吭。
直到他走過來,輕輕把我抱在懷里:
「露出點破綻吧,讓我知道你也在想我。」
時至今日,我還記得落在我肩頭的那抹溫熱。
往事浮現,宋延知的眼圈一點點變紅。
我看著兩行清淚沿著他銳利的輪廓滑下來,心里竟有一瞬間的暢快。
可暢快之后,又被無盡的悲哀掩蓋。
我們,怎麼就走到這一步了?
10
那天以后,宋延知不再逃避,離婚流程很快就走完了。
財產大部分都是按照協議的方式分割,宋延知拿出兩千萬,買下了我手中的股份。
領證那天,辦事人員借口打印機沒紙,讓我和宋延知再商量商量。
ADVERTISEMENT
他坐在一邊,一言不發。
就這樣過了一個小時,那人看我倆實在沒有復合的意思,才無奈地在離婚證上扣下鋼印。
走出民政局,宋延知攔住我:
「陳妍,如果你將來有什麼困難,你可以……」
哪怕到這一刻,他還是覺得我必須依附他才能活。
其實這些日子以來,我不斷在想一個問題——
宋延知為什麼會那麼輕易就出軌呢?
本質上來說,是他從沒有把我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尊重我。
這麼多年,我在他眼里不過是人生的附庸、是占有的社會資源、是獲得勝利的獎賞勛章。
他認為只要給我他的愛,就可以成為我的上帝。
哪怕出軌被發現,只要哄一哄,我也總會妥協。
就像波伏娃在《第二性》里說過的:
【權力歸于男性,女性僅僅是附庸。附庸的庇護來自權力,歧視也來自于權力。】
更可悲的是,社會上的大多數男人都是這麼想的。
這套畸形的游戲規則,千百年來從未變過。
陽光刺眼,我卻并不遮擋,反而適時打斷他:「管好你自己,不必操心我。」
手機震動一下,楊涵打來電話。
說約到了投資人,讓我趕快坐她派的車過去。
正奇怪她為何特意強調「她派的車」這四個字,一個帥得慘絕人寰的西裝帥哥就從車上下來了:
「陳小姐,我是小張,來接您去酒店。」
短暫錯愕后,我應聲說好。
上車前,卻被一臉陰沉的宋延知抓住車門。
他的薄唇緊抿,從嘴里擠出幾個字:「什麼酒店?」
我淡然抬頭:「和你沒關系了吧?」
宋延知手一僵,我趁勢關上了車門。
后視鏡里,熟悉的身影漸行漸遠。
他就那樣僵在原地,一動不動,任秋風打著旋兒從他身邊掠過,卷起一地枯葉。
我聽見撥浪鼓的聲響,伴著孩童咯咯的笑聲。
也聽見草木和真菌,在枯葉下奮力滋長。
一年又一年。
仿佛生命只有輪回,沒有終點。
小張打開音箱,電臺正在播放《我的未來式》。
他告訴我,《愛情公寓》已經播放到大結局。
我忽然想起和宋延知窩在出租屋吃泡面追劇那幾年。
那時我不理解婉瑜的離開,只感嘆有情人為何不能終成眷屬。
直到這一刻跳出婚姻的枷鎖,我終于能夠理解她、成為她。
我把手伸出窗外,感受風的凜冽和自由。
不多時,小張從前方遞來一張紙巾:「陳小姐,您哭了。」
哭了嗎?我揩拭掉臉上的淚痕:
「瞇眼了。」
「那我關上窗戶。」
「不用。」我阻止他,「就這樣吹著吧,很舒服。」
11
為了股價,宋延知封鎖了離婚的消息,只對外宣稱我退出公司架構。
我也不計較,靠著賣股權的錢,和楊涵合伙開了家公司。
半年后趕上國家扶持,站在政策的風口上賺得飛起。
一次酒會,我又遇到了當初說我比宋延知會來事的那位老板:
「宋太太,哦不對,現在應該叫您陳總。」
「短短一年,您可真是讓我刮目相看。」
他笑著遞給我一杯香檳,言語間頗有欣賞。
作為陳妍被人尊重的感覺,一如既往地不錯。
我舉杯。
敬他,也敬我。
……
準備拓展規模時,宋延知和我看上了同一個項目。
他提出一起建設,還拿出了一份可行性很強的企劃書,胸有成竹的模樣像是準備了很久。
我讓風險組和項目組評估了一下,確實利潤可觀,再加上宋延知愿意讓渡兩個點給我,我更沒有理由反對。

 上一章
上一章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